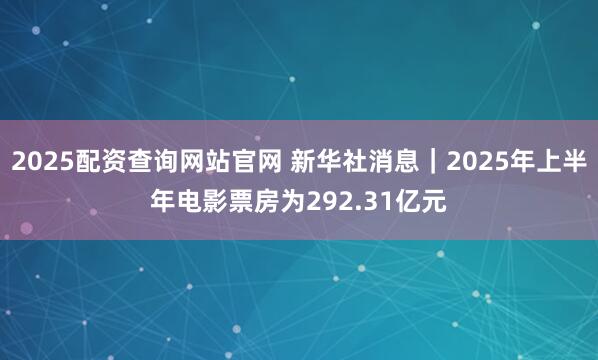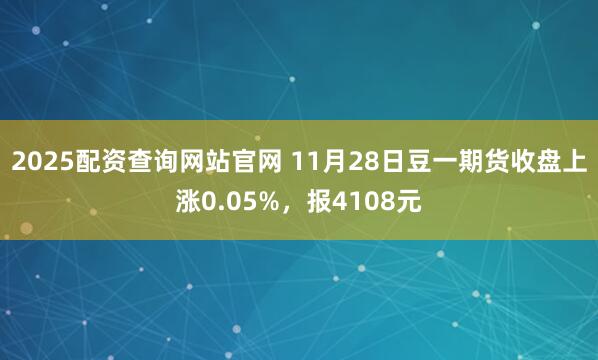蒋经韬
手机屏上倏然亮起的,是程远斌老师的回信。此时此刻,我正被人潮推拥着,挤进这城市清晨“早高峰"的地铁里。周遭是金属的摩擦声与人群的絮语,一片扰攘的喧闹。然而,我盯着屏幕看完这几行字,仿佛被来自另一个世界吹来的一缕清风笼罩,这风里带着稻花的微香与泥土的润泽,霎时便将这方寸之间的嘲杂,隔绝开了。
“蒋总的随笔气势磅礴,撼人心魄!为家乡立言,为家乡而歌,够味!蒋总有您家祖辈蒋祥墀的才气韬略,不易呀!我家祖辈百年前就珍藏蒋祥墀一件珍宝,如同神器,故我家才有今天!”
我捧着手机,除了感动还有一丝牵挂一一这个与共和国同龄的老人现在过得好吗?
思绪渐渐飘散开,越过钢筋水泥的丛林,飞往江汉平原的腹地,天门九真的乡野。此刻的先生,是在哪一片稻花香里,写下这慷慨的嘉许呢?我想象着,那定是几间粉墙黛瓦的农舍,静静地卧在一条清浅的小河湾旁。屋前有一方平整的晒场,几只油亮的鸡雏,正悠闲地啄食着散落的谷粒。一条黄犬,许是老了,懒懒地趴在竹篱下,尾巴偶尔轻扫一下飞过的蝇虫。而先生,或许就坐在一株老槐树下的石凳上,身后的屋檐下,还挂着几串金黄的玉米与火红的辣椒。晨露未晞,田畴里漫上来的是潮润的、混合着腐草与新禾气息的风。他的手机屏幕,便在这浑厚的、充满生命元气的背景里,亮着微光。那不是一个退休官员的颐养,也不是一个落魄文人的归隐,那是一种“回归”,像一颗饱含生命力的种子,终于落回了它本该生长的土壤里,从容,安详,而又充满了内在的、向上的力量。
展开剩余80%这想象,让我心头一热。人生的缘分,真是说不清,道不明,仿佛一条地下暗河,你以为它早已干涸在岁月的沙石之下,它却会在某个不经意的时刻,于你脚边,重新汩汩地涌出清泉。
我的记忆,便沿着这泉流,溯回到了许多年前。那该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某一天了,在古城荆州,我与几位天门干驿的同乡,由荆州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天门干驿老乡杨忠洲先生组织,一同驱车前往巴东,去拜访时任县委书记的程老师。那时的他,主政一方,眉宇间是挥斥方遒的锐气,言谈中是经世济民的抱负。然而,即便是在那政务倥偬的官衙里,他与我们谈得最投机的,竟还是文学。我清晰地记得,他谈及正在创作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荆楚枭雄陈友谅》时,那双眼睛里迸发出的光,那是一种超越了现实政务的、对于历史烟云与人性幽微的痴迷与探索。那光,与我后来在作家协会里见到的他,是一脉相承的。
后来,他果真调任湖北省作家协会,任副书记、副主席。从一方父母官,到一省文坛的掌舵者,这身份的转换,于他仿佛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。那文学的梦,似乎从未在他心中熄灭,只是暂时被现实的职责所掩映,一旦得了机会,便又熊熊燃烧起来。那时的我,却正陷入人生与事业的湍流之中。新闻业态经历着从传统网媒到自媒体的剧烈转折,如同大地震后的版块迁移,一切都处在失序与重建的恐慌里。我像个溺水的人,只顾着在信息的洪流中拼命划水,以求不被淹没,那份对于文学的静穆之心,早已被冲刷得七零八落。于是,与程老师的联系,便也几乎中断了。现在想来,那并非疏远,而是一种自惭形秽的躲闪,怕自己满身的尘泥与疲惫,扰了那书斋的清净。
人生的轨迹,如同两股线,时而并行,时而远离,却又总在命定的某个节点,重新交织。差不多是疫情之前的某年某月某日,我们在一个文学活动中久别重逢了。那时的程老师,好像刚刚退休不久。岁月在他身上,似乎并未刻下多少衰颓的痕迹,只是将那曾经的锐气,磨洗得更为温润、宽厚。我们面对面地谈了很久,谈文学,谈故土,谈这些年来彼此错过的光阴。活动结束后,是我开车送他回的寓所。车行驶在华灯初上的城市高架上,窗外是流光溢彩的、永不疲倦的都市之夜。而程老师坐在副驾驶座上,语调平和,却带着一种难以抑制的热情,向我描绘他心中的蓝图。他说,他要回天门九真老家去,不再只是做一个闲居的寓公,而是要办一个自然生态、历史文化与时代元素融合一体的现代农庄!
我听了,先是愕然,随即一股巨大的兴奋与钦佩,便如暖流般涌遍全身。这兴奋,并非因为这是一个多么宏大的商业计划,而是因为它所指向的一种生命姿态。我想到了陶渊明,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,那是一种决绝的、个人主义的退守,是对于污浊官场的彻底背弃,从而在山水间寻得个体灵魂的安顿。然而,程老师的回归,却并非一种“退”。他的“归去来兮”,不是要回到一个与世隔绝的桃花源,而是要建设一个向世界开放的、充满生机的“新乡土”。这便远高于那位古代的隐逸诗人了。陶渊明的归宿是“守”,守住自己的一方心田;而程老师的志向是“创”,创造一片可以滋养乡邻、传承文脉的沃土。他不是要从世界中逃离,而是要将外部世界的精华——那些先进的技术、理念与时代精神——引回故土,与那里的自然生态、历史文化进行一次深度的、创造性的融合。这是一种积极的入世,是“退”于官场名利之后,更宏大、更根本的“进”。他的生命情怀,因而具有了一种陶渊明所不具备的建构性与时代担当。这不再是独善其身的清高,而是兼济乡土的赤诚。
没想到,更有奇迹在后头。2025年4月,我收到《竟陵文学》春季号纸质版。
这期杂志的头条“名家有约"栏目,刋登了执行主编张有为先生向我约的三篇散文稿。在我阅读到封三的时候,突然发现了一条消息:市作家协会一行参观子文山风景区。我看到了“程远斌"三个字。仔细一看,这个子文山风景区,就是当年程先生给我讲的文旅项目。消息说,2025年新春伊始,程先生主导策划的子文山风景区正式启动建设了。
这个风景区总占地面积近千亩,项目规划依据岗地鱼塘地理优势,利用已有的古树参天,花木扶疏,合理布局山、洞、水、木交错相间的景区景观有子文山和藏酒窖,月亮湾和碾子岛,农耕地和书院。力争将其建设成为集观光休闲、读书美食、文化研讨、文学创作为一体的农文旅景区。景区内设置天历史人文墙和民俗饮食文化街。
76岁的程先生还希望市作协把子文山景区作为创作基地,期望市内外的作家们抒发热爱故乡的情怀,讲好天门故事。
看到这一消息,我非常兴奋!为程先生的情怀与信念,更为程先生的执着与执行力!
我马上在微信里,给程先生发去了截图和真挚的祝贺!
程先生在微信里,盛情邀请我到景区做客指导!
——这点点滴滴的思绪,在地铁车轮有节奏的轰鸣声中,纷至沓来,如汤如沸,让我不能自已。我急需将这份澎湃的心潮记录下来,诉诸笔端。于是,就在这颠簸行进的车厢里,在无数陌生而疲惫的面容之间,我掏出手机,写下了下面这封回信:
尊敬的程老师:
收到您鼓励的微信文字,心中满是无可言喻的温暖与感激。那寥寥数语间,自有磅礴的气度与深切的期许盘旋,让我既感奋然,又深觉惭愧——这已不单单是文字上的知音之赏,更是文脉相承的确认,是师长对后辈如父如兄般的殷殷嘱托。
您一直是我文学与人生的楷模,一座立在远方、却始终照亮我内心道路的灯塔。当年拜读您的长篇历史小说《荆楚枭雄陈友悯》,那于历史夹缝中重构的恢弘叙事,那灌注于人物命运里的深厚人文关怀,早已在我年轻的心版上,刻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。而更令我敬佩无已的,是您退休之后,毅然决然回归天门故土,勤耕垄亩的抉择。您以最质朴、也最坚实的行动,诠释着一个中国文人最本真的担当。这不仅是为振兴桑梓尽一份智识与力气,更是将“精神还乡”这个古老的母题,升华为一种对土地的敬畏与生命实践。在您身上,我看到了“道在伦常日用之中”的真义。
说来真是惭愧,我心底一直觉得,是欠着您一篇文章的——一篇关于您的文章,关于我们之间这份跨越了漫长岁月与不同人生际遇的师生情谊,关于天门这片厚土所赋予我们共同的精神基因与胎记。特别是在得知您于老家正倾心打造那座融汇古今的文化庄园、构筑新时代的精神家园之后,这个愿望便愈发强烈,日夜灼烧着我的心。我期盼着,能在年内觅得一个闲暇,亲赴九真,到您的府上拜会。我渴望在那片由您精心耕耘的土地上,赤足感受它的温度,呼吸它的气息,让灵魂接受一场彻底的洗礼。唯有如此,我方能完成这篇迟来太久的致敬。
您在信末提及祖辈祥墀公的旧事,令我深受触动,几欲堕泪。百年的光阴流转,程蒋两家的情谊,早已如那地下的根脉,丝丝缕缕,交织融汇于天门这片文化的厚土之中。而您今日对我的这份期许,正是这份古老情谊在新时代温暖而有力的回响。我当以先贤的风范为镜,时刻照见自身的不足;更以您的风骨为尺,丈量前路的每一步。在文学与人生的漫漫长途上,我必将以此自勉,继续求索,不敢有负于这薪火相传的微光。
期待早日与您相见,在家乡的清风明月之下,共话桑麻,再聆教诲。
学生 蒋经韬 敬上
2025年10月10日上午8时至9时
于赴文华学院授课之8号地铁转11号地铁上
信写完了,地铁也恰好到站。我随着人流走出车厢,重新汇入地面的人群潮水之中。然而2025配资查询网站官网,我的心,却仿佛有一部分留在了那片想象中的稻花香里。我知道,在那遥远的故乡,有一位长者,正以他最沉静又最热烈的方式,书写着一部关于土地、文化与生命归来的史诗。而我在这城中所写下的每一个字,都不过是对那部伟大史诗的、一声微弱的回响罢了。但这回响,因了那份“神交”与传承,便也有了它自身的重量与光芒。
发布于:湖北省金富宝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